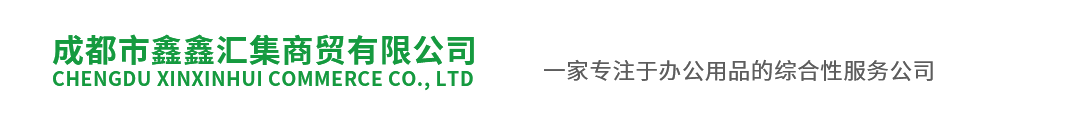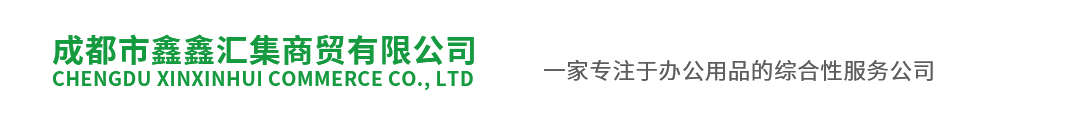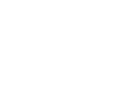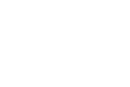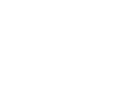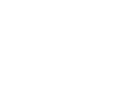上世纪七十年代,谁有时机把日子中的瞬间定格成相片留作留念?是摆摊的小商贩,是体系内的干部,仍是在部队执役的武士?翻阅现在尚存的这些老相片,咱们清楚明了,大多数记载里的人物来自体系内的干部与武士集体。由于武士转业、退伍后,往往会持续进入体系内担任干部,所以那个年代真实能握着相机、把宝贵时间留存下来的人,往往是体系内的人。与此同时,乡镇上的一般人家,若想具有一张像样的相片,往往要阅历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——相机、胶卷、冲印的花费,都是那个时期难以跨过的门槛。
七十年代的我国,没有全面实施市场经济,社会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探索调整,商人阶级没有真实兴起或遍及到普一般通的家庭的视界之中。因而,商人摄影留念的场景在其时显得分外稀疏,他们的身影常常只呈现在极少数的写实镜头里,更多时分仍是以“邻里合作、日常小事”的方法被记载,而不是作为年代回忆的主角呈现。
那时的农人兄弟姐妹们仍然日子窘迫,日复一日为了温饱奔走忙碌。能有一点点闲暇去照张相、留作留念,几乎是一种奢华。胶卷和冲印的本钱像一座看得见的山,放在家庭的预算之外,因而,往常人家里的相片多是宝贵且稀缺的珍品。摄影的时机往往与严重节日、婚嫁或村社活动挂钩,更多时分仍是在城里亲朋来访、或遇到走运的部队时才有的回忆片段。
我家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农人,他人生中的第一张相片,是在九十年代初才有时机留存下来的。相同,我母亲也是六十年代出世的,她的第一张相片则是在八十年代才拍照完结。咱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,是在1998年拍照的。翻看那些相片时,年月的痕迹与亲情的温度交错在一起,心里总会被一股说不出的感动牵引。那些旧照像是跨过时空的信笺,提示咱们爱惜眼前的每一个一般日子。
人生呀,怎么会这么容易变老?韶光呀,为何不愿倒流,让咱们再度走回芳华的年少年月?爸爸妈妈现在都已步入六十余年的年岁,步态渐慢,健康时有些崎岖,听力与视力也在不同程度上退化。至于我自己,头发已逐步斑白,成为一个一般的中年人。每次陪同他们谈起幼年往昔,他们都会显露绚烂的笑脸,似乎又回到了那些年少无忧的韶光,连言语都带着温暖的光。
这组老相片拍照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相片中的多是年青男人,细心分辩,大多数人应与军旅生计严密相关。他们身躯垂直,气质沉稳,站在前时,脸上的骄傲感像一道激烈的光,照射着其时的年代自傲。
前的年青小伙子们,身躯垂直,胸膛挺得像要顶起一片天,目光专心而坚决,神态显显露一种教人服气的严肃与骄傲,似乎在向国际宣告他们所担负的任务。
上海黄浦江畔的留影,拍照于1978年12月。相片边际那排带着年代印记的笔迹,简练却极具艺术美感,言外之意似乎都在叙述那一段前史的气味。那些字的笔画干净利落,是非比照清楚,给人一种意境深远的美。
年青的武士形象分外夺目。他头戴军帽,身穿整齐的戎衣,概括清楚的线条与耸立的身姿,透出一股非凡的气质与纪律感,让人似乎能听见他们在风中昂扬的标语与脚步声。
在公园的古建筑前留影的年青武士,布景的亭台楼阁、回廊及石径,构成了一幅静寂而严肃的画面。阳光斜射,影子拉得细长,似乎把年青的芳华与前史的厚重一起镶嵌在镜头里,给人以永久的回忆。
年青干部在古城门前留影,门楼的砖石纹路明晰可辨,门楣上或许还残藏着当年的符号与题字。人们的姿势各异,有的侧身看向镜头,有的正面凝视前方,给这张相片增加了多层次的情感与故事感。
相同是在古建筑前的年青干部留影,镜头捕捉到他们天然的表情与奇妙的情感改变。穿着整齐、表情沉着,似乎在记载一种工作的自傲与对未来的等待。
另一组在现代大桥前留影的年青武士,布景的桥梁线条现代而具有力气感,与他们年青的肌肉线条彼此照射,整张相片透出一种年代的跨过感,像在标志性地告知人们:新时期的我国正在兴起。
最终,在古亭台前合影的年青干部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一位胸前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。那些钢笔并非一般文具,而是一种标志——干部的标配,代表着职责、笔记与指令的权利标志。相片中的他们神态仔细,目光坚毅,似乎在提示后人:记得把职责写在纸上,把抱负埋在心中。